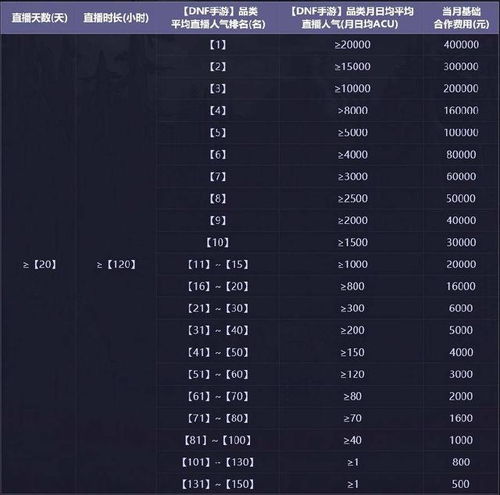文学的历史能动性怎么样(杨操和杨述华什么关系)
- 明星八卦
- 2022-12-29 05:49:30
- -
让历史的复杂性在文学研究中显影 ——刘复生的学术与思想 “理解历史总是伴随着理解自己的冲动,因为这是一个理解历史和理解自我的双重过程”。 在一次学术访谈中,刘复生如是说。确实,历史与个体是同构的:历史的脉动总是由处身其间的个体所承担,时代给每个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而这一点在知识分子的身上表现地尤为明显:学者的生命史、学术史总是和宏大历史扭结在一起。由此,对我们来说,读懂一个学者,也就读懂了他身上承载的历史。 尽管学界对“70后”的代际划分不甚合理,但刘复生仍然被认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众多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中,刘复生突破了文学研究的局限,将研究领域从中国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更广泛的思想史与文化研究,观点新锐且切中要害,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不少的惊喜和冲击。近年来,刘复生的研究成果颇丰,不仅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文,还陆续出版了《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思想的余烬》以及《文学的历史能动性》等学术论著。 我们无法精细地描绘一个时代的文化地形图,却可以勾勒出一个学者的思想肖像。恰如贺桂梅解读刘复生的论文标题“激活历史经验与学术知识的力量”,在刘复生的各种论述中,他多次表明了自己的理念:文学研究者不能自外于时代,去追求“纯文学”的海市蜃楼;而是要反求诸己,将自己的感受、经验、知识投入文学研究,使主体与时代对话,使文学与历史互动。在刘复生的学术世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文学具有“历史能动性”。文学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工具,也是改造世界的实践。在语言秩序改变的同时,生活世界的面貌也将焕然一新。 以文学为对象、以文学研究为志业,刘复生不仅完成了对文学的阐释和意义的构建,还完成了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 一、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 刘复生是个“非典型”的70后学者,这一个案的特殊性似乎使“70后”的命名显得颇为尴尬。事实上,较之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出生于1970年的刘复生更多地分享了60年代末学者的历史经验。正是年龄的差异,使他的经验与大多数70后学者不同,更具有“之间”的特质。他没有经历过“文革”,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高中和大学中文系,在“学习时代”接受了“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影响,但作为青年学生,他并不像启蒙知识分子是时代的主体,而是局外的旁观者。进入90年代,激进的市场化改革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文化气氛,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构成了巨大的反差。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学者经历的是这个转折的结果,刘复生则经历了转折的全过程,对时代的风向转换心有戚戚焉。 这是历史的巨变在个体身上的投影,也暗中决定了刘复生学术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视野。一方面,他带有80年代浓厚的“文学介入社会”的情感残留;另一方面,由于他的学术生涯起步于90年代,也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犬儒主义态度。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研究生毕业之后曾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工作过五年,其后再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受业于洪子诚先生。在这个意义上,他并不是“从学院到学院”的学者,而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从事电视剧创作的经历,无疑影响了他其后的研究路径和学术方向。 孟子谓:“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之所以在此处冗言刘复生的人生履历和历史清单,是因为上述生命史的铺陈与其后刘复生学术的展开密切相关。换言之,在刘复生的身上,个体的历史经验不仅构成了生命史的一部分,也构成了学术史的原材料。在80年代与90年代之间,在学院与电视台之间,刘复生以“主体的同一性”将感受、经验与知识的碎片加以整合加工,将经验重新知识化 从而搭建出自己的学术大厦。贺桂梅由此将刘复生放置在“后-新启蒙”知识谱系 之中,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坐标系。 在刘复生的诸多论述中,我们能很清晰地辨别,他的学术大厦建立在两个基座之上:一方面,是对90年代以来(包括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小说的阐释和研究;另一方面,是对80年代“新启蒙”知识体系和文学制度的批判。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缺一不可,是对位关系。尽管刘复生尚未对80年代进行系统的考察,但在他所有的研究之中,80年代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一个状如幽灵般的巨大而迷魅的存在。在他的单篇论文中,则用浓度很大的笔墨写下了对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思考。 《历史的浮桥———世纪之交“主旋律”小说研究》(河南大学2005年版)由刘复生在北大毕业的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也是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而刘复生关于“主旋律”小说的研究还在继续,其中包括正在进行的国家社科项目《“主旋律”文学的创作现状与发展走向》以及其他“主旋律”影视作品的评论。 这无疑是一个需要学术勇气的题目,也必然招致许多误解。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当然和刘复生多年的电视台工作经验有关。他在工作过程中遭遇了大量当代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制度和规则,因为这份“局内人”的熟悉,剖析起来自然游刃有余。但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这个题目则显得“不那么文学”(或者说挑战了文学场域中的“潜规则”)。“必也正名乎”,要研究“主旋律”小说必须先说明研究对象的价值所在,但作为“尴尬的文坛地位与暧昧的文学史段落” ,“主旋律”小说却一直被认为是没有文学价值的作品。自从80年代以来,关于“什么是文学”,文学场域对此已有了明确的界定。在“新启蒙”主义思潮的统摄下,“纯文学”的神话被建构出来,“‘政治性’、‘意识形态’、‘商业性’是文学的原罪,含有‘非文学’、‘反审美’的本性” 。在此二元论的框架中,政治/文学、意识形态/审美、通俗/精英、官方/民间构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而恰恰是这一系列二元关系中的后项占据了文学评价体系中的象征资本,从而压抑了二元关系中的前项。“主旋律”小说作为研究对象,正处在文学场域的边缘和大众文化场域的主流这两个相互矛盾的位置上。 但刘复生显然无意做一项所谓的“纯文学”研究,更何况单纯的审美研究根本无法说明“主旋律”小说中问题的核心。在他那里,文学研究已经和文化研究与思想史相结合。同时,他还回到了思考的原点:历史与文学的辩证法。他试图探索的是,摒弃掉80年代形成的关于“去历史性”的“纯文学的洁癖”以及判断是否为“文学”的认识性装置 (这一装置本身构成了新的压抑与遮蔽),我们能否转换提问方式,去追问:为什么要生产“主旋律”小说?原因或许是不言自明的——这是90年代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文化生产领域的控制。那么,“主旋律”诞生的历史语境以及政治、文化背景是什么?“主旋律”小说是怎样被创作和接受的?意识形态层面的宏观操作是如何“下降”到文本细部的? 在《历史的浮桥》中,刘复生回答了上述问题。在他看来,“主旋律”是一项“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战略工程”,“它的使命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申政党的合法性,同时,利用富于技巧性的意识形态叙事,对新时代所产生的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中种种内在的社会矛盾加以弥合,以消除政治的不确定因素,并造就适应新的国家政治、经济需要的具有‘现代’特质的历史主体。” 在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主旋律”的提倡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多元化”的新语境中试图重新“一体化”,获取“文化领导权”的努力。一方面,它要从正面宣扬“合法性”,询唤出新的历史主体;另一方面,它要弥合矛盾,维持社会的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政治统治与文化领导权是同构的,都具有重构权威、整合社会、增加国民认同的功能。而要达到上述的效果,意识形态的叙事无疑需要“富于技巧性”。 就此而言,刘复生的研究无比艰难,他需要穿过种种意识形态制造的幻象,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内部构造,从而到达“真实的荒漠”和“坚硬的内核”。 这是一个复杂的思辨过程,但也标志着刘复生作为学者的成熟。在绪论与第一章中,刘复生勾勒出“主旋律”遭遇的现实境况与意识形态转型的语境,进而考察“主旋律”小说创作与接受的情况。在这倾向制度研究的两个部分,刘复生在看似枯燥无味的政策文献中看出了历史的动态与趋势,其中又以对“一体化”、“多元化”和“主旋律”关系的讨论极为出彩,这集中体现在绪论的第三节“‘新意识形态’与‘一体化’历史遗产”里。 在洪子诚先生的当代文学史框架中,他通过对各种文学力量此消彼长的分析,勾勒出50—70年代的“一体化”进程以及这个体系在80年代解题成为“多元化”的线索,由此奠定了当代文学的整体框架,这是一个前30年和新时期文学有着连带感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一体化”到“多元化”,是一个从整合到解体的过程。 但是,当时间进入90年代后,这种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主旋律”的出现构成了对“多元化”的矫正与反拨,并与80年代之前“一体化”构成某种呼应关系 。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意味着“多元化”之后的另一个阶段。这是一副新的历史图像,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刘复生的论点在洪子诚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90年代出现的“新意识形态”,一方面“维护旧有的社会主义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另一方面将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从传统的社会主义形象转移到经济增长和维护国家稳定上去。由此,“主旋律”必须创造一种新的表意机制,将旧有的意识形态与新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从而跨越两者之间的断裂地带。 而在“主旋律”这个新的整合框架中,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留下了缝合的缝隙。新旧意识形态的耦合绝非那么顺畅,而是充满结构性的矛盾。意识形态的叙事无论多么“富于技巧性”,总难免留下创口和空隙。《历史的浮桥》的第二至五章正是通过症候式的阅读和批判性的阐释去暴露文本的缝隙。刘复生按照题材划分,将“新乡土小说”、“新改革小说”、“反腐败”小说、“军事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展开论述。通过扎实的文本细读与叙事分析,刘复生将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推进到文本细部。在刘复生看来,“主旋律”小说文本是各种话语互相竞逐,各种意义互相博弈的场所,“‘主旋律’文学以一种更为集中、更为戏剧化方式包含了这个时代的文学秘密。” 用文本细读的方式进行话语分析,是将政治与诗学整合起来研究的表现,由此,刘复生打破了传统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二分法,为意识形态批评的文本分析方法做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在刘复生的学术中,历史建构和文本细读构成了鲜明的风格,但一个更为明显的特征却是理论建构。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研究者中,刘复生学术的理论性是很浓的。《历史的浮桥》中,我们不难看到刘复生“理论干预”的热情。但难得的是,他在历史、文本与理论之间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 。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刘复生使用理论的方法。尽管他受过北大了严格的学院训练和“后学”洗礼,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思想脉络中亦可以明显看出洪子诚与戴锦华两位老师的痕迹,但是他并未做理论的炫技和堂皇的梦呓,而是懂得“藏理论的技术”。确实,明目张胆地引用西方诸位后学大师,确实可以挟洋自重故作高深,但半生不熟的翻译腔与古怪的中文表达只会让读者高山仰止的同时望而却步。懂门道的读者不难在刘复生的书中看出福柯、阿尔都塞、葛兰西、齐泽克对他的影响,但这般高屋建瓴却又深藏不露却是十分难得的。就这点而言,抑或是深受其师洪子诚的影响。 在《历史的浮桥》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复生对“主旋律”小说所持的主要是批判态度。而他对“主旋律”小说的追踪还在继续。《历史的浮桥》主要考察的是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主旋律”小说,而新世纪文学的“主旋律”创作则让他看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他认为,“某些被称为‘主旋律’的创作可以有新的升华,至少一部分‘主旋律’文学应超越一般的主流意识形态书写的层面(包括在创作上和主流意识形态保持距离),在文化政治的意义上通过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叙述开发出中国文化的‘普遍性’价值” 。在他的愿景中,与现实生活对话的、描述中国经验的、表达对未来的想象力的文学才是伟大的“中国文学”;较之格局狭小的“纯文学”,近期的“主旋律”创作则凸显了这个可能 。 经由“主旋律”小说的研究,刘复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领土”,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历史、文本、理论的结合,对政治/审美二元论的辩证,文学史向思想史与文化研究的拓展——这些都是刘复生苦心孤诣经营的结果。在这项尚在持续且“未完成”的工作中,刘复生奠定了自己的学术风格、思想风格和文体风格。确实,在刘复生的“主旋律”小说研究中,他将问题意识贯穿其间,既有历史的挖掘又有思想的辩证。历史的种种悖论经由他繁复的思辨,如同剥洋葱一般,层次和面向历历分明。值得注意的还有他的语言,他的论述简洁而朴素、庄重而文雅。他无意追求华丽和铺张的句子,而是着力凸显思想本身的诗意。而他使用的诸如“历史的天真”“理性的狡计”等术语也充满了智性的乐趣。 二、“为了聚会的告别”:文学研究的跨界与回归 虽然是北大中文系当代文学的科班出身,但刘复生却有着从学科内部“出逃”的热情。“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但我却越来越不务正业,成为这一专业领域内一个心不在焉的眺望者。” 在言辞中,刘复生表达了他对文学的态度,其中也难掩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失望。作为一个学院建制下的研究者,这样的说法难免让人吃惊;但对刘复生而言,却有着“自己转变学术研究方向的内在逻辑”和“寻求并确认自己在这个时代以学术为志业的理由” 。在他那里,阐释世界也是阐释自己的生命,这是一个理解外部也理解自身的解释学过程。当初他投身文学专业,正是抱着“为生命赋予价值和意义”的期望,而彼时的文学正满足了他的这份托付。那时的文学对于他,既是一种美学和语言形式,又是个体生命依托的容器,为他提供了稳定的意义世界。这是他与文学之间的“约定”。然而,时移事往,当代文学在商业大潮和自我掣肘中萎靡不振,陷入了危机和困局;而此时的刘复生也开始反思“文学的位置”,将注意力转移到更能托付他生命期望的领域中去。 “为了聚会的告别”。刘复生未必对当代文学一往情深,他当初念兹在兹的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文学所承载的历史能量:一种未来的想象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另类的视野。简言之,是一种“切入当代世界的能力” 。然而,随着“当代文学”的学科建制愈发严密,当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原有的能量与活力。于是,刘复生开始了自己的突围。但是,无论哪位学者,“跨界”都是一次自我重新蜕变的艰难过程——多年的学术训练和学科规训,已然在个体身上养成了思维习惯和路径依赖。“跨界”,俨然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一次知识与书写上的转型。 但刘复生的转身却是如此地顺理成章。他的学术视野扩大了,问题意识却是一以贯之的。他将关注点投向历史学、社会学、哲学,他将研究领域从当代文学史拓展到思想史与文化研究。面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现象和知识领域,刘复生用多重的跨界演绎了学者身份的吊诡——学院/反学院、文学/文化政治、书斋/社会,他展示了思想者与文化游击者的亲缘性,他是一个书斋中的革命者,尽管在不同的领域自在游戈,但不变的是他对中国经验的关注和对发声位置的自觉。正因为这份“发声位置的自觉”,他才不会迷失在暧昧的文学—文化现象和复杂的政治光谱中。 跨界之后,则是回归。依旧是文学的界面,随着刘复生新视角的切入,却显露了具有差异性的面向。刘复生将文学研究与思想史以及文化研究相结合 ,使文学研究产生了新的阐释路径,由此也展示了文学研究新的“历史能动性”。 《反思八十年代:“新启蒙主义”文学态度及其文学实践》是刘复生学术中的里程碑式的论文,曾被多次转载。在这篇论文中,他显露了对80年代的反思以及对“新启蒙主义”和“纯文学”的批判。刘复生通过对思想史与文学史关系的谱系学考察,打破了80年代的文学神话。他认为,“新启蒙主义”直接塑造了80年代的文学实践,文学只不过是“新启蒙主义”在文学领域的延长线,是“新启蒙主义”的一个感性化的形态。 这一思潮对文学实践的巨大塑形力量,是当时文学界的批评家们用文学批评呼唤和催生的。然而,刘复生更为激越且颠覆性的思考则在于:“新启蒙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单一影响遮蔽了80年代文学的其他可能性,它窄化和压缩了文学创作的空间,从而构成了另一种压抑机制。它的“人道主义”与“主体性”使得作家仅仅注重个人自由,而忽视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从而为90年代文学“由‘大写的人’向‘小写的人’(欲望化的个人)的转化”埋下了伏笔。由此,80年代在表面上“去政治化的文学实践”恰恰是以一种最政治化的方式显露出来——“所谓反抗‘文学的工具论’,事实上致使以另一种工具论(‘新启蒙主义’的工具)来替代旧有的政治工具论。” 在刘复生这里,思想史与文学史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而是盘根错节环环相扣。他将文学生产放置在文化政治的场域中进行分析,用历史还原的方式重构了80年代的知识—权力与文学创作的镜像关系,使得我们对延续至今的“纯文学”神话有了全新的理解和感悟。 这是一种“历史作为解构路径”的方法论。刘复生在重现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解构了某些不言自明的、被后设的认识论装置、被思想的取景框遮挡在视野外部的东西。“我是惟一一个逃出来向你报信的人”, 这毋宁是一种文学研究的游击战——“破”,在文学神话最坚固、最保守的地方进行解构,拆卸那看似铁板一块的论述,解放被遮蔽与被压抑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所强调的“历史的复杂性”,不仅没有破坏文学的美感,反而是解放了我们的感性 。“文学批评就是要破坏我们的正常感觉” ,这是刘复生所写下的警句。神话/解构,这是另一重意义上的“复魅”,与“祛魅”不同,刘复生打破单一框架,追求多元,在历史的细节中救赎文学的想象力和可能性。他在多篇论文中使用了这种极具破坏性的方法,其中包括《先锋小说:改革历史的神秘化——关于先锋文学的社会历史分析》。与《反思八十年代》的理论建构相得益彰的,这篇论文在80年代一个看似“纯文学”的文学现象中找到了庖丁解牛的可能。在刘复生看来,“先锋小说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现代化命运的曲折隐喻,那些似乎完全抽空现实内容的形式实验,或刻意将主题抽象化、普遍化以脱离中国现实的现代主义情绪,背后隐约而片段地浮现着的仍是当代中国的历史性焦虑和愿望。” 而这些暧昧难明的“寓言”却被“新启蒙主义”的意识形态披上了“纯文学”的外衣,获得了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 同样是使用解构策略,除了上述对单个思潮和现象进行的考察,刘复生还擅长在历时性线索中追踪某一文学现象,例如《穿越历史的“青春之歌”――意识形态变迁及﹤青春之歌﹥的再叙述》、《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前篇论文中,他使用“再解读”的文本比较方法,通过考察当代史上不同时间点对小说《青春之歌》的改写来凸显意识形态的变迁。“通过分析这些文本之间相互替换、交叠的演化转迹,我们可以隐约勾勒出一条当代观念史的变迁线索及其内在逻辑。” 在这里,文本成为档案,成为各个时代意识形态的投影、国民情感结构的证据。这一不断改编和重写的经典文本穿越了整个当代历史,见证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和意义阐释之间的隐秘联系。而在后篇论文中,刘复生则阐发了新世纪以来“新革命历史小说”与十七年写作模式之间的关系,继承、拓展、改写成为他这项研究的关键词。他论述在“告别革命”的语境下,旧有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资源中如何在现实境况中产生回响。这份社会主义的遗产的复活乃是新意识形态作用下进行的新的历史阐释,“折射的是普遍的社会焦虑与民众潜在的政治诉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批评”在刘复生学术世界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理论使用的难度却不在理论自身,而是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相结合,与中国经验相结合。中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不言自明,但刘复生却在重重的雾障中树立自己笃定的发声位置,他深入意识形态的内在肌理,暴露意识形态形塑自身的内在逻辑。这一工作是困难的、也是具有挑战性的。在他的研究中,当代史、思想史构成了思考的宏观背景,文化研究构成了展开细部论述的方法。“他从不认定有某种先在的、天生的意义存在,因而总是去关注这个意义如何被建构出来的过程。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关注,使他深入到复杂的历史关系场域中,描述各种力量的博弈以及策略性的结果” 他的思考浸润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由此也对历史中主体的位置格外敏感。他深知主体是被历史所形塑的,命运的偶然性与个人的遭际可能会阻挡个体对真理的认知。看似自由的个体其实并不独特,而是被历史裹挟其中,是时代的人质。由此,他也“否思” 自己的发声位置,将自己置入复杂的政治光谱之中,尊重差异、尊重其他立场与论述。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派别论争中,他是一位持重且稳健的学者,并未因站队而为某种立场背书,有对于自我位置的警醒和自嘲。作为“后-新启蒙”世代的学者,他对未曾亲历的文革、神话的80年代、漫长的90年代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洞察,而这些历史洞察也形塑了他的学术与他的主体。 但刘复生却不满于已然定型的思维框架,他是一个不断追求自我突破与自我超越的学者。他的论文中不时显露出自嘲和反讽的幽默,这种幽默是谦逊的表现,他不满于既有的学术成果,而是始终处在漫长的“学习时代”。他要在背景的转换中调整自己的立场和发声位置,要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资源和学术方法来耕种自己的园地,要不断确认自我投身文学(超克文学)的初衷。感受、经验与知识,在他那里是不断更新不断发展的。由此,他在阐释他人也在阐释自身,在他者身上看到自我的镜像 。由此,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他写过那么多评述师友的文章,因为阅读他人,不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亦是一个自我确认的过程。他者与自我是相互激励相互触发的。在《思想的余烬》和《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中,刘复生都辟专辑来收纳自己所写的这部分文章。其中尤以《文学的历史能动性》中收入的三篇为代表。 《想象一个新世界——韩少功的政治哲学》是一篇很见功力的文章。刘复生在这篇论文中考察了韩少功这位思想型作家散文中蕴涵的政治智慧,挖掘出韩少功在文学创作之外的另一面向。我们常常会叹服西方作家作品中深度意涵,并因此为中国文学自卑。但刘复生告知我们,中国也有思想型作家,只是未被批评者阐发出来而已。他这篇角度颇为奇特的论文正是要做出这方面的努力。他论述韩少功超克非此即彼的辩证法、“完美的假定”、对完美人性和民族主义的看法等等。刘复生徜徉在韩少功的思想世界中,采撷思想的珍珠。作家繁复的思辨需要批评者同样的智性和觉悟才能达到,批评家必须与作家是“平视”的、等值的。由此,刘复生也在论述的同时挖掘了自身对时代的见解,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既是评述,也是阐发,这是一个批评家学术创造性的体现。在《在这个时代如何做一个人文学者——汪晖的意义》中,刘复生的评议则不仅显露对汪晖的认同,更暴露出他的自我焦虑与希翼。汪晖超学科的综合能力和研究中显露的鲜明的当代意识让刘复生深受启发,也让刘复生跳出狭隘的专业领域,走向跨界和超越。在《穿越语言 图绘历史——解读贺桂梅》一篇,刘复生则将贺桂梅作为“70后”世代的代表,从“精神资源与知识谱系”、“研究领域与学术风格”、“人生经验与立场、追求”几个方面较为完整地评述了师姐贺桂梅的学术成就。由于他与贺桂梅分享了某些共同的经验,这篇论文带上了他精神自传的色彩,他在贺桂梅的身上看到某种自己的镜像。 而在《思想的余烬》中,则收入了刘复生另外一些评述师友的文章,研究对象包括洪子诚、韩毓海、耿占春、李少君、单正平、程光炜等等。这些师友是刘复生考察的对象,同时刘复生也在这些对象中投射了自己对文学、对历史与世界的看法。这些文章既是刘复生的学术生涯“中途的报告”,也为我们提供了一副当代知识人的精神图谱和读书清单。 然而,个人命运的偶然遭际不仅是遇见一些人,还有与一个地方的缘分。博士毕业之后,刘复生先是在山东一所高校就职,其后辗转到海南大学任教。近身的人和事由此也成为刘复生学术灵感的来源,关于海南,他出版了《海南当代新诗史稿》,写作了《记忆与变迁:红色娘子军与当代女性的政治策略》等单篇论文。这种在地和在场的研究,给刘复生以新的机遇和挑战。在这些研究中,他处理了自身经验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从而在原有的学术领域内另辟了新的疆场。而这岛屿经验与大陆经验的对话,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跨界与回归? 三、当代文学研究何为?当代文学批评何为? 随着刘复生学术经验的增加,他逐渐在一些“务虚”的话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独到的看法。这些论述和观点充满了“破坏与重建”的激情,在这个意义上,刘复生或许可称为“当代文学”的“搅局者”,一个拆解成规破除偏见的释梦者。刘复生不屑于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学者,他的思想的冲击力在于“解构神话”和反向思维。面对日益边缘化的当代文学,他折返思考的原点,追问和质询当代文学本体性的问题:什么是当代文学?什么是当代文学研究?什么是当代文学批评? 这是当代文学的危机时刻。当代文学在社会场域中的边缘化,原因不仅来自商业和市场的冲击,还来自当
创作主体有相应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体现为受动性和能动性。受动性指的就是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要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的创作一般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同样具有能动性,即创作主体既要受到时代、社会的限制,又有其个人的主动性,体现了创作主体能动性的一面。这种能动性表现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还是可以根据其个人的思想认识、艺术趣味、生活经验,来选择他所要表现和能够表现的生活、主题、题材和体裁,还可以选择他所熟悉的艺术技巧和方法。即使时代、社会、传统的影响,
一方面,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基础,受动性对能动性是一种制约,人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特定的能动性,都是以某种受动性的制约为依据的;另一方面,能动性又成为受动性的主导,人通过自觉的生产劳动来发展、完善自己,提高对受动性的认识和对受动性的控制能力。 一 ,文学反映的受动性
文学反映的受动性是指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从这点上来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学反映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产物,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而人民的社会生活则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这就从哲学角度,从根本上阐释了文学的受动性。
那么,为什么文学反映具有受动性即源于社会生活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呢?
首先,社会生活中的劳动为文学活动、文学反映提供了前提条件。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活动,是一切其它活动的前提。这一方面在于人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才能从事其它活动,另一方面就在于人就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生成的,恩格斯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
其次,社会生活产生了文学活动、文学反映的需要。人的活动都伴随着一个自觉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又是为某种需要而设定的。黑格尔告诉我们,人的需要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需要,不仅在于人的需要的种类以及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而且还在于对人来说每一种具体的需要又都可以生发出更加细微和更加特殊的需要。其中,对文学活动、文学反映的需要则是人的一般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追求具体表现为人类渴望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和全面地表现自己生命活动的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②。 人要改变外在世界,在外在事物中复现自己的冲动即自由创造的冲动。史前人类在集体进行的社会生活中,为了协调行动,交流情感与信息,减轻疲劳等,就由这些需要产生了语言和最初的文学。鲁迅先生曾对此作过通俗化的解释,他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③ 这一表述形象地说明了劳动中的需要直接促成了文学的产生。
再次,社会生活构成了文学反映的主要内容。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存在。远古时代遗存的作品中大都描写了当时人们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击壤歌》中写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他写出了早期农耕生活中人们自给自足,随遇而安的历史情况。《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仅仅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但生动地写出了制作武器去狩猎的过程。由此可看出,社会生活构成了文学反映的主要内容。
最后,社会生活制约了早期文学的形式。各民族最早的文学体裁是诗,而诗在当时是必须吟唱的,而且它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来传达。因此,早期的文艺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结合体。这种早期文艺的形式同劳动过程直接相关。原始人将劳动动作和被狩猎的动物的动作衍化为舞蹈,劳动时的号子与呼喊发展为诗歌,而劳动时发出的各种声音和体现的节奏则为原始人提供了音乐的灵感。诗,乐,舞三位一体实则是劳动过程中这几种艺术形式的萌芽因素统一在一起的反映。 文学反映的受动性是指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从这点上来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学反映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产物,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而人民的社会生活则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这就从哲学角度,从根本上阐释了文学的受动性。 创作主体有相应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体现为受动性和能动性。受动性指的就是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要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的创作一般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同样具有能动性,即创作主体既要受到时代、社会的限制,又有其个人的主动性,体现了创作主体能动性的一面。这种能动性表现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还是可以根据其个人的思想认识、艺术趣味、生活经验,来选择他所要表现和能够表现的生活、主题、题材和体裁,还可以选择他所熟悉的艺术技巧和方法。即使时代、社会、传统的影响,
一方面,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基础,受动性对能动性是一种制约,人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特定的能动性,都是以某种受动性的制约为依据的;另一方面,能动性又成为受动性的主导,人通过自觉的生产劳动来发展、完善自己,提高对受动性的认识和对受动性的控制能力。
一方面,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基础,受动性对能动性是一种制约,人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特定的能动性,都是以某种受动性的制约为依据的;另一方面,能动性又成为受动性的主导,人通过自觉的生产劳动来发展、完善自己,提高对受动性的认识和对受动性的控制能力。 一 ,文学反映的受动性
文学反映的受动性是指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从这点上来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学反映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产物,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而人民的社会生活则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这就从哲学角度,从根本上阐释了文学的受动性。
那么,为什么文学反映具有受动性即源于社会生活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呢?
首先,社会生活中的劳动为文学活动、文学反映提供了前提条件。人类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活中的最基本活动,是一切其它活动的前提。这一方面在于人要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才能从事其它活动,另一方面就在于人就是在这种生产活动中生成的,恩格斯说,劳动“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
其次,社会生活产生了文学活动、文学反映的需要。人的活动都伴随着一个自觉的目的,而这一目的又是为某种需要而设定的。黑格尔告诉我们,人的需要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需要,不仅在于人的需要的种类以及满足需要的手段的多样性和特殊性。而且还在于对人来说每一种具体的需要又都可以生发出更加细微和更加特殊的需要。其中,对文学活动、文学反映的需要则是人的一般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追求具体表现为人类渴望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和全面地表现自己生命活动的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说 “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②。 人要改变外在世界,在外在事物中复现自己的冲动即自由创造的冲动。史前人类在集体进行的社会生活中,为了协调行动,交流情感与信息,减轻疲劳等,就由这些需要产生了语言和最初的文学。鲁迅先生曾对此作过通俗化的解释,他说:“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动,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是‘杭育杭育派’”。③ 这一表述形象地说明了劳动中的需要直接促成了文学的产生。
再次,社会生活构成了文学反映的主要内容。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存在。远古时代遗存的作品中大都描写了当时人们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击壤歌》中写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他写出了早期农耕生活中人们自给自足,随遇而安的历史情况。《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仅仅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但生动地写出了制作武器去狩猎的过程。由此可看出,社会生活构成了文学反映的主要内容。
最后,社会生活制约了早期文学的形式。各民族最早的文学体裁是诗,而诗在当时是必须吟唱的,而且它以载歌载舞的方式来传达。因此,早期的文艺是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结合体。这种早期文艺的形式同劳动过程直接相关。原始人将劳动动作和被狩猎的动物的动作衍化为舞蹈,劳动时的号子与呼喊发展为诗歌,而劳动时发出的各种声音和体现的节奏则为原始人提供了音乐的灵感。诗,乐,舞三位一体实则是劳动过程中这几种艺术形式的萌芽因素统一在一起的反映。 文学反映的受动性是指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同时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从这点上来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文学反映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头脑中的产物,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而人民的社会生活则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性质和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性质和变化。这就从哲学角度,从根本上阐释了文学的受动性。 创作主体有相应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体现为受动性和能动性。受动性指的就是作家在文学创作活动中要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他的创作一般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作家同样具有能动性,即创作主体既要受到时代、社会的限制,又有其个人的主动性,体现了创作主体能动性的一面。这种能动性表现在,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作家还是可以根据其个人的思想认识、艺术趣味、生活经验,来选择他所要表现和能够表现的生活、主题、题材和体裁,还可以选择他所熟悉的艺术技巧和方法。即使时代、社会、传统的影响,
一方面,能动性以受动性为基础,受动性对能动性是一种制约,人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任何一种特定的能动性,都是以某种受动性的制约为依据的;另一方面,能动性又成为受动性的主导,人通过自觉的生产劳动来发展、完善自己,提高对受动性的认识和对受动性的控制能力。
本文由作者笔名:手机用户90264 于 2022-12-29 05:49:30发表在本站,原创文章,禁止转载,文章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本文链接:https://www.3m3q.com/mx-14024.html
 手机用户90264
手机用户902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