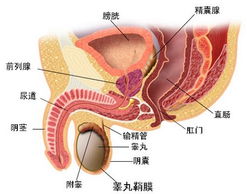有谁推荐几部七八十年代的台湾老电影(台湾绝版杀妻电影)
- 影视
- 2023-03-15 04:24:01
- -
小城故事、小毕的故事、悲情城市、汪洋中的一条船、八百壮士、窗外、雁儿在林梢、儿子的大玩偶、搭错车、在水一方、看海的日子、杀夫、雪在烧、欢颜、庭院深深、金盏花、大哥大等等
台湾老电影:
《搭错车》1983年
《望海的母亲》1986年
《鲁冰花》1989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1984年 1981年侯孝贤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他独树一帜,大胆运用长镜头而造就出的独特视觉风格,后来则成了他电影作品的一项重要标记。随后他又推出了<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年)他在这种复述青春与童真的过程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其惯有的长镜头视觉模式,悠长而沉闷,所以并没有人给他下过一个肯定的结论。而到了1984年则有了转机,随着他拍摄技术的日臻完善,作品<风柜来的人>推出后,使他获得了空前的好评,此时舆论界才算是首肯了其固守的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一些国际国内的奖项,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风柜来的人>所呈现的是一个平静、悠闲的渔村景象,主人公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他们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终于有一次,他们把事情闹得太大,而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风柜——这个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小岛,他们栖息的家,来到了光怪陆离的高雄,一切都变了,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茫然、陌生、焦虑和恐惧。在两种生活状态的切换中,侯孝贤的想传达的心绪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孩童和少年时代的那种幻梦般的执迷,是这个时期侯孝贤电影的一大创作特点,即使是一些细琐闲杂的小趣,他都会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距离和角度,去倾注自己情怀与关注。希望——失望,失望——希望,那种沾染着稚气面对着成长体验的情结,成为他早期作品里最重要的基调。也正如他自己所体验的那样:“莫如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温暖,但带着距离,所以更需要绝对的清醒。”
从<儿子的大玩偶>(1983年)中对宠溺娇纵的享受,到<冬冬的假期>(1984年)里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与现实的初步领悟,侯孝贤总是在利用着孩子们的视觉与思考,来发掘并且披露现实生活背后的一些创痕与阴影。充满了彷徨与无奈的岁月里,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拙劣地过活,然而孩子们却是无辜的,他们的眼睛中居然也衍生了不知所措的神色。人们都在找寻着奔忙下去的理由,那么又有谁来为孩子们解释清楚,那些他们根本看不太懂的林林总总,究竟都是在为了些什么。
<童年往事>(1985年)中,这种微妙的情结仍旧在继续着,不同于以往的是这种情结似乎已经有所依托,其实这种依托的端的和源头,则更多是来自于他自己一些成长经历。又是一个兀长的镜头给过来,我们看到那少年(侯孝贤)精赤着脚站在芒果树下,整个街道非常寂寥。远远传来脚踏车吃力轮转声,声音如此微弱,分不清脚踏车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树下面是一个独立世界,有人出来转一圈,一会儿又不见。坐在树上的少年侯孝贤清醒地感受到微热的风,安静的蝉声,人的活动 。他突然感到寂寞。好像时空整个凝结在那里……
我们在<童年往事>里,看到的是自己幼年时候玩耍过的游戏,蹲在门口等大人回来的经验,吃到一根雪糕的喜悦……这些琐碎的、平淡的,似乎只会吸引小孩子的情节累积起来,渐渐地打动了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从<恋恋风尘>(1986年)中的顾盼与滞等,到<尼罗河的女儿>(1987年)中的徇徇不羁与突然死亡,我们忽而发现了侯孝贤对于爱情观念的一种决绝与虚妄。而<<悲情城市>(1989年)的涌现,就已经把他那决绝的哀与乐、生与死的情结,完全地超越了童真与爱情的零碎表白。故事中再现了那个幻灭的时代,男与女、大与小、老与少,都混沌在一种从无奈到绝望的状态里生存着。与其是说那个令人痛至决绝的城市充满悲情,莫不如说是人们对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焦虑与绝望,生离——死别,死别——生离,或许在这种伤情的故事里,唯一能令人畅释心胸的画面,也只有那长镜头下的远山近水……
陶醉在长镜头的古典写实形式,或许会是侯孝贤今生今世都无法放弃的情怀,而对于现实生活与田园野趣的执迷,也源自于其写实个性下的完整经验。而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在秉执这种特质,但是他这种写实的特质却与侯孝贤的乡土田园气韵截然相反,他把故事的触角牢牢地扎在了台湾城市的最深处,总是在揭批着那些披着改良外衣的生活与人性,揭开人性最卑微、最晦暗、最阴冷的最底层。
与侯孝贤一样,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启始于那些孩提时代的意趣与感悟。在最初<光阴的故事——指望>(1982年)中,他并没有过于偏执地坚守批判与怀疑的态度,而仅只是对于懵懵懂懂的青春,作了一次最委婉、最浅显、而又是最单纯的解读。女中学生淡淡的相思,在含蓄和缓慢的画面中给予呈现,既没有伤害,也没有冲突,只有那留存在记忆中的一幕幕可供回味的瞬间,在细腻的呓语声中向你委婉道白。道白这无奈的青春,体会这“光阴的故事”。
在随后的<海滩的一天>的创作中,这种天真、烂漫的情怀忽然原离了他的视线,一股迷惘而空虚的落寞情结,弥盖了他对爱情与生活的幻梦与憧憬。故事的调子饱涵着沉重,那种原离了生活环境,而又揭示着现象的侧面写实,把一种对人性的怀疑推到了观众们的面前。身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空洞而虚伪的社会环境下,人际关系足逐渐变得疏离、冰冷,任何情感与允诺都显得无比苍白而毫不可信。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链条,紧禁地捆绑着彷徨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每一个年轻人,爱没有了希望,恨也就无所谓痛快,生活自然而然地也就被搁置到了一种更加极端、更加边缘的状态。
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发展到<青梅竹马>(1985年)与<恐怖分子>(1986年),则成为更教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大都会五光十色的物质环境,只会更加剧这些个人的绝望与无助。<海滩的一天>毕竟在剧终时成就了两个独立而成熟的女性,而到了<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死亡、空虚的概念却展开了更为悲观的结论。到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更是延伸了<恐怖分子>的社会败德和软弱人性的“共犯”控诉。小四的杀人行为,被拓宽为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封闭,以至于对纯洁、真诚的扼杀。如此看来,若说杨德昌是一位当代台湾社会道德观察省思者,也并不为过。 1981年侯孝贤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他独树一帜,大胆运用长镜头而造就出的独特视觉风格,后来则成了他电影作品的一项重要标记。随后他又推出了<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年)他在这种复述青春与童真的过程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其惯有的长镜头视觉模式,悠长而沉闷,所以并没有人给他下过一个肯定的结论。而到了1984年则有了转机,随着他拍摄技术的日臻完善,作品<风柜来的人>推出后,使他获得了空前的好评,此时舆论界才算是首肯了其固守的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一些国际国内的奖项,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风柜来的人>所呈现的是一个平静、悠闲的渔村景象,主人公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他们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终于有一次,他们把事情闹得太大,而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风柜——这个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小岛,他们栖息的家,来到了光怪陆离的高雄,一切都变了,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茫然、陌生、焦虑和恐惧。在两种生活状态的切换中,侯孝贤的想传达的心绪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孩童和少年时代的那种幻梦般的执迷,是这个时期侯孝贤电影的一大创作特点,即使是一些细琐闲杂的小趣,他都会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距离和角度,去倾注自己情怀与关注。希望——失望,失望——希望,那种沾染着稚气面对着成长体验的情结,成为他早期作品里最重要的基调。也正如他自己所体验的那样:“莫如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温暖,但带着距离,所以更需要绝对的清醒。”
从<儿子的大玩偶>(1983年)中对宠溺娇纵的享受,到<冬冬的假期>(1984年)里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与现实的初步领悟,侯孝贤总是在利用着孩子们的视觉与思考,来发掘并且披露现实生活背后的一些创痕与阴影。充满了彷徨与无奈的岁月里,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拙劣地过活,然而孩子们却是无辜的,他们的眼睛中居然也衍生了不知所措的神色。人们都在找寻着奔忙下去的理由,那么又有谁来为孩子们解释清楚,那些他们根本看不太懂的林林总总,究竟都是在为了些什么。
<童年往事>(1985年)中,这种微妙的情结仍旧在继续着,不同于以往的是这种情结似乎已经有所依托,其实这种依托的端的和源头,则更多是来自于他自己一些成长经历。又是一个兀长的镜头给过来,我们看到那少年(侯孝贤)精赤着脚站在芒果树下,整个街道非常寂寥。远远传来脚踏车吃力轮转声,声音如此微弱,分不清脚踏车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树下面是一个独立世界,有人出来转一圈,一会儿又不见。坐在树上的少年侯孝贤清醒地感受到微热的风,安静的蝉声,人的活动 。他突然感到寂寞。好像时空整个凝结在那里……
我们在<童年往事>里,看到的是自己幼年时候玩耍过的游戏,蹲在门口等大人回来的经验,吃到一根雪糕的喜悦……这些琐碎的、平淡的,似乎只会吸引小孩子的情节累积起来,渐渐地打动了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从<恋恋风尘>(1986年)中的顾盼与滞等,到<尼罗河的女儿>(1987年)中的徇徇不羁与突然死亡,我们忽而发现了侯孝贤对于爱情观念的一种决绝与虚妄。而<<悲情城市>(1989年)的涌现,就已经把他那决绝的哀与乐、生与死的情结,完全地超越了童真与爱情的零碎表白。故事中再现了那个幻灭的时代,男与女、大与小、老与少,都混沌在一种从无奈到绝望的状态里生存着。与其是说那个令人痛至决绝的城市充满悲情,莫不如说是人们对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焦虑与绝望,生离——死别,死别——生离,或许在这种伤情的故事里,唯一能令人畅释心胸的画面,也只有那长镜头下的远山近水……
陶醉在长镜头的古典写实形式,或许会是侯孝贤今生今世都无法放弃的情怀,而对于现实生活与田园野趣的执迷,也源自于其写实个性下的完整经验。而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在秉执这种特质,但是他这种写实的特质却与侯孝贤的乡土田园气韵截然相反,他把故事的触角牢牢地扎在了台湾城市的最深处,总是在揭批着那些披着改良外衣的生活与人性,揭开人性最卑微、最晦暗、最阴冷的最底层。
与侯孝贤一样,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启始于那些孩提时代的意趣与感悟。在最初<光阴的故事——指望>(1982年)中,他并没有过于偏执地坚守批判与怀疑的态度,而仅只是对于懵懵懂懂的青春,作了一次最委婉、最浅显、而又是最单纯的解读。女中学生淡淡的相思,在含蓄和缓慢的画面中给予呈现,既没有伤害,也没有冲突,只有那留存在记忆中的一幕幕可供回味的瞬间,在细腻的呓语声中向你委婉道白。道白这无奈的青春,体会这“光阴的故事”。
在随后的<海滩的一天>的创作中,这种天真、烂漫的情怀忽然原离了他的视线,一股迷惘而空虚的落寞情结,弥盖了他对爱情与生活的幻梦与憧憬。故事的调子饱涵着沉重,那种原离了生活环境,而又揭示着现象的侧面写实,把一种对人性的怀疑推到了观众们的面前。身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空洞而虚伪的社会环境下,人际关系足逐渐变得疏离、冰冷,任何情感与允诺都显得无比苍白而毫不可信。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链条,紧禁地捆绑着彷徨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每一个年轻人,爱没有了希望,恨也就无所谓痛快,生活自然而然地也就被搁置到了一种更加极端、更加边缘的状态。
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发展到<青梅竹马>(1985年)与<恐怖分子>(1986年),则成为更教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大都会五光十色的物质环境,只会更加剧这些个人的绝望与无助。<海滩的一天>毕竟在剧终时成就了两个独立而成熟的女性,而到了<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死亡、空虚的概念却展开了更为悲观的结论。到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更是延伸了<恐怖分子>的社会败德和软弱人性的“共犯”控诉。小四的杀人行为,被拓宽为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封闭,以至于对纯洁、真诚的扼杀。如此看来,若说杨德昌是一位当代台湾社会道德观察省思者,也并不为过。
《搭错车》1983年
《望海的母亲》1986年
《鲁冰花》1989年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1984年 1981年侯孝贤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他独树一帜,大胆运用长镜头而造就出的独特视觉风格,后来则成了他电影作品的一项重要标记。随后他又推出了<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年)他在这种复述青春与童真的过程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其惯有的长镜头视觉模式,悠长而沉闷,所以并没有人给他下过一个肯定的结论。而到了1984年则有了转机,随着他拍摄技术的日臻完善,作品<风柜来的人>推出后,使他获得了空前的好评,此时舆论界才算是首肯了其固守的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一些国际国内的奖项,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风柜来的人>所呈现的是一个平静、悠闲的渔村景象,主人公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他们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终于有一次,他们把事情闹得太大,而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风柜——这个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小岛,他们栖息的家,来到了光怪陆离的高雄,一切都变了,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茫然、陌生、焦虑和恐惧。在两种生活状态的切换中,侯孝贤的想传达的心绪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孩童和少年时代的那种幻梦般的执迷,是这个时期侯孝贤电影的一大创作特点,即使是一些细琐闲杂的小趣,他都会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距离和角度,去倾注自己情怀与关注。希望——失望,失望——希望,那种沾染着稚气面对着成长体验的情结,成为他早期作品里最重要的基调。也正如他自己所体验的那样:“莫如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温暖,但带着距离,所以更需要绝对的清醒。”
从<儿子的大玩偶>(1983年)中对宠溺娇纵的享受,到<冬冬的假期>(1984年)里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与现实的初步领悟,侯孝贤总是在利用着孩子们的视觉与思考,来发掘并且披露现实生活背后的一些创痕与阴影。充满了彷徨与无奈的岁月里,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拙劣地过活,然而孩子们却是无辜的,他们的眼睛中居然也衍生了不知所措的神色。人们都在找寻着奔忙下去的理由,那么又有谁来为孩子们解释清楚,那些他们根本看不太懂的林林总总,究竟都是在为了些什么。
<童年往事>(1985年)中,这种微妙的情结仍旧在继续着,不同于以往的是这种情结似乎已经有所依托,其实这种依托的端的和源头,则更多是来自于他自己一些成长经历。又是一个兀长的镜头给过来,我们看到那少年(侯孝贤)精赤着脚站在芒果树下,整个街道非常寂寥。远远传来脚踏车吃力轮转声,声音如此微弱,分不清脚踏车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树下面是一个独立世界,有人出来转一圈,一会儿又不见。坐在树上的少年侯孝贤清醒地感受到微热的风,安静的蝉声,人的活动 。他突然感到寂寞。好像时空整个凝结在那里……
我们在<童年往事>里,看到的是自己幼年时候玩耍过的游戏,蹲在门口等大人回来的经验,吃到一根雪糕的喜悦……这些琐碎的、平淡的,似乎只会吸引小孩子的情节累积起来,渐渐地打动了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从<恋恋风尘>(1986年)中的顾盼与滞等,到<尼罗河的女儿>(1987年)中的徇徇不羁与突然死亡,我们忽而发现了侯孝贤对于爱情观念的一种决绝与虚妄。而<<悲情城市>(1989年)的涌现,就已经把他那决绝的哀与乐、生与死的情结,完全地超越了童真与爱情的零碎表白。故事中再现了那个幻灭的时代,男与女、大与小、老与少,都混沌在一种从无奈到绝望的状态里生存着。与其是说那个令人痛至决绝的城市充满悲情,莫不如说是人们对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焦虑与绝望,生离——死别,死别——生离,或许在这种伤情的故事里,唯一能令人畅释心胸的画面,也只有那长镜头下的远山近水……
陶醉在长镜头的古典写实形式,或许会是侯孝贤今生今世都无法放弃的情怀,而对于现实生活与田园野趣的执迷,也源自于其写实个性下的完整经验。而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在秉执这种特质,但是他这种写实的特质却与侯孝贤的乡土田园气韵截然相反,他把故事的触角牢牢地扎在了台湾城市的最深处,总是在揭批着那些披着改良外衣的生活与人性,揭开人性最卑微、最晦暗、最阴冷的最底层。
与侯孝贤一样,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启始于那些孩提时代的意趣与感悟。在最初<光阴的故事——指望>(1982年)中,他并没有过于偏执地坚守批判与怀疑的态度,而仅只是对于懵懵懂懂的青春,作了一次最委婉、最浅显、而又是最单纯的解读。女中学生淡淡的相思,在含蓄和缓慢的画面中给予呈现,既没有伤害,也没有冲突,只有那留存在记忆中的一幕幕可供回味的瞬间,在细腻的呓语声中向你委婉道白。道白这无奈的青春,体会这“光阴的故事”。
在随后的<海滩的一天>的创作中,这种天真、烂漫的情怀忽然原离了他的视线,一股迷惘而空虚的落寞情结,弥盖了他对爱情与生活的幻梦与憧憬。故事的调子饱涵着沉重,那种原离了生活环境,而又揭示着现象的侧面写实,把一种对人性的怀疑推到了观众们的面前。身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空洞而虚伪的社会环境下,人际关系足逐渐变得疏离、冰冷,任何情感与允诺都显得无比苍白而毫不可信。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链条,紧禁地捆绑着彷徨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每一个年轻人,爱没有了希望,恨也就无所谓痛快,生活自然而然地也就被搁置到了一种更加极端、更加边缘的状态。
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发展到<青梅竹马>(1985年)与<恐怖分子>(1986年),则成为更教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大都会五光十色的物质环境,只会更加剧这些个人的绝望与无助。<海滩的一天>毕竟在剧终时成就了两个独立而成熟的女性,而到了<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死亡、空虚的概念却展开了更为悲观的结论。到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更是延伸了<恐怖分子>的社会败德和软弱人性的“共犯”控诉。小四的杀人行为,被拓宽为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封闭,以至于对纯洁、真诚的扼杀。如此看来,若说杨德昌是一位当代台湾社会道德观察省思者,也并不为过。 1981年侯孝贤拍出第一部长片<就是溜溜的她>,他独树一帜,大胆运用长镜头而造就出的独特视觉风格,后来则成了他电影作品的一项重要标记。随后他又推出了<在那河畔青草青>(1982年)他在这种复述青春与童真的过程中,他仍然没有放弃其惯有的长镜头视觉模式,悠长而沉闷,所以并没有人给他下过一个肯定的结论。而到了1984年则有了转机,随着他拍摄技术的日臻完善,作品<风柜来的人>推出后,使他获得了空前的好评,此时舆论界才算是首肯了其固守的电影艺术表现形式,一些国际国内的奖项,也给他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转机。
<风柜来的人>所呈现的是一个平静、悠闲的渔村景象,主人公阿清和同伴们成天无所事事,他们看白戏、赌博、逞勇斗狠。终于有一次,他们把事情闹得太大,而被警方惩戒,于是结伴离开风柜——这个澎湖列岛中的一个小岛,他们栖息的家,来到了光怪陆离的高雄,一切都变了,他们对这个城市感到茫然、陌生、焦虑和恐惧。在两种生活状态的切换中,侯孝贤的想传达的心绪是不言而喻的。
对于孩童和少年时代的那种幻梦般的执迷,是这个时期侯孝贤电影的一大创作特点,即使是一些细琐闲杂的小趣,他都会以一种近乎偏执的距离和角度,去倾注自己情怀与关注。希望——失望,失望——希望,那种沾染着稚气面对着成长体验的情结,成为他早期作品里最重要的基调。也正如他自己所体验的那样:“莫如一个俯瞰人世的旁观者。温暖,但带着距离,所以更需要绝对的清醒。”
从<儿子的大玩偶>(1983年)中对宠溺娇纵的享受,到<冬冬的假期>(1984年)里对自然与社会、生活与现实的初步领悟,侯孝贤总是在利用着孩子们的视觉与思考,来发掘并且披露现实生活背后的一些创痕与阴影。充满了彷徨与无奈的岁月里,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拙劣地过活,然而孩子们却是无辜的,他们的眼睛中居然也衍生了不知所措的神色。人们都在找寻着奔忙下去的理由,那么又有谁来为孩子们解释清楚,那些他们根本看不太懂的林林总总,究竟都是在为了些什么。
<童年往事>(1985年)中,这种微妙的情结仍旧在继续着,不同于以往的是这种情结似乎已经有所依托,其实这种依托的端的和源头,则更多是来自于他自己一些成长经历。又是一个兀长的镜头给过来,我们看到那少年(侯孝贤)精赤着脚站在芒果树下,整个街道非常寂寥。远远传来脚踏车吃力轮转声,声音如此微弱,分不清脚踏车从哪里来又要往哪里去。树下面是一个独立世界,有人出来转一圈,一会儿又不见。坐在树上的少年侯孝贤清醒地感受到微热的风,安静的蝉声,人的活动 。他突然感到寂寞。好像时空整个凝结在那里……
我们在<童年往事>里,看到的是自己幼年时候玩耍过的游戏,蹲在门口等大人回来的经验,吃到一根雪糕的喜悦……这些琐碎的、平淡的,似乎只会吸引小孩子的情节累积起来,渐渐地打动了我们身边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
从<恋恋风尘>(1986年)中的顾盼与滞等,到<尼罗河的女儿>(1987年)中的徇徇不羁与突然死亡,我们忽而发现了侯孝贤对于爱情观念的一种决绝与虚妄。而<<悲情城市>(1989年)的涌现,就已经把他那决绝的哀与乐、生与死的情结,完全地超越了童真与爱情的零碎表白。故事中再现了那个幻灭的时代,男与女、大与小、老与少,都混沌在一种从无奈到绝望的状态里生存着。与其是说那个令人痛至决绝的城市充满悲情,莫不如说是人们对自己命运与前途的焦虑与绝望,生离——死别,死别——生离,或许在这种伤情的故事里,唯一能令人畅释心胸的画面,也只有那长镜头下的远山近水……
陶醉在长镜头的古典写实形式,或许会是侯孝贤今生今世都无法放弃的情怀,而对于现实生活与田园野趣的执迷,也源自于其写实个性下的完整经验。而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在秉执这种特质,但是他这种写实的特质却与侯孝贤的乡土田园气韵截然相反,他把故事的触角牢牢地扎在了台湾城市的最深处,总是在揭批着那些披着改良外衣的生活与人性,揭开人性最卑微、最晦暗、最阴冷的最底层。
与侯孝贤一样,杨德昌的电影作品也启始于那些孩提时代的意趣与感悟。在最初<光阴的故事——指望>(1982年)中,他并没有过于偏执地坚守批判与怀疑的态度,而仅只是对于懵懵懂懂的青春,作了一次最委婉、最浅显、而又是最单纯的解读。女中学生淡淡的相思,在含蓄和缓慢的画面中给予呈现,既没有伤害,也没有冲突,只有那留存在记忆中的一幕幕可供回味的瞬间,在细腻的呓语声中向你委婉道白。道白这无奈的青春,体会这“光阴的故事”。
在随后的<海滩的一天>的创作中,这种天真、烂漫的情怀忽然原离了他的视线,一股迷惘而空虚的落寞情结,弥盖了他对爱情与生活的幻梦与憧憬。故事的调子饱涵着沉重,那种原离了生活环境,而又揭示着现象的侧面写实,把一种对人性的怀疑推到了观众们的面前。身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空洞而虚伪的社会环境下,人际关系足逐渐变得疏离、冰冷,任何情感与允诺都显得无比苍白而毫不可信。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链条,紧禁地捆绑着彷徨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每一个年轻人,爱没有了希望,恨也就无所谓痛快,生活自然而然地也就被搁置到了一种更加极端、更加边缘的状态。
这个疏离、冰冷的人际关系发展到<青梅竹马>(1985年)与<恐怖分子>(1986年),则成为更教人恐惧悲观的软弱道德行为,大都会五光十色的物质环境,只会更加剧这些个人的绝望与无助。<海滩的一天>毕竟在剧终时成就了两个独立而成熟的女性,而到了<青梅竹马>和<恐怖分子>,死亡、空虚的概念却展开了更为悲观的结论。到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更是延伸了<恐怖分子>的社会败德和软弱人性的“共犯”控诉。小四的杀人行为,被拓宽为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封闭,以至于对纯洁、真诚的扼杀。如此看来,若说杨德昌是一位当代台湾社会道德观察省思者,也并不为过。
本文由作者笔名:wuxia68 于 2023-03-15 04:24:01发表在本站,原创文章,禁止转载,文章内容仅供娱乐参考,不能盲信。
本文链接:https://www.3m3q.com/ys-61214.html
 wuxia68
wuxia68